马上注册,查阅更多信息
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,没有账号?立即注册
x
小说已“死”过多次,这次“杀死”它的是女性?
一位匿名的评论家在英国最新一期的《评论家》(The Critic)杂志上发表文章称英文小说正在衰落。这位作者给出了三个原因:首先是作家都缺乏写作技巧,即使读过创意写作班,50岁以下的作家即使连对话也写不好。其次是整个出版市场变得十分势力,文学性较强的小说被平庸之辈拒之门外。TA认为英国当代承袭的文学图景看低了威廉·博伊德(William Boyd)这样的作家。第三个原因是小说的人物不再为那些最普遍的道德问题所困扰,宗教话题也不会再成为小说的主题。“身份政治认同”代替了以前小说中严肃的普遍性问题。TA讽刺道:“现在小说主人公遇到的最棘手的道德问题只是’这周和谁睡’。”
这篇评论批评了《白牙》作者扎迪·史密斯,说她的对话特色只是会用斜体,还批评了《正常人》作者萨莉·鲁尼,认为其小说中的对话充满了严苛的教条主义。作者还为萨莉·鲁尼感到可惜,她不到30岁就能写出两部有趣的小说,但接下来要花费10年的时间从评论者挖的陷阱中走出来,言外之意,大家并没有给出中肯的评价,萨莉·鲁尼受到了浮夸风尚的影响。
正因为扎迪·史密斯和萨莉·鲁尼都是女性,这篇评论招来了女性专栏作家瑞安·露西·科斯莱特(Rhiannon Lucy Cosslett)的质疑,她从这篇评论中读出了仇视女性作家的味道,总结出“这次是女性杀死了小说”的结论。她说自己已经读过太多“小说的讣闻”,但好像小说的命比猫咪还要多一些。她认为这两位女性作家打破了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惯常思维,她们受到的不同寻常的欢迎程度招来了这些人的嫉妒。其次她反驳道,不是小说衰落了,而是现在的作家不按照以前公认的标准进行写作了,写作的道路本来就应该是多元的。
科斯莱特的态度要乐观一些,她认为现在小说虽然处于“苍白”的状态,但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“没人希望男性白人作家灭亡,只希望他们能给其他性别或少数族裔作家留出些发展余地。”
LGBT文学
石墙暴动(The Stonewall Riots)已经过去51周年。在这51年间,LGBT群体为我们创造了更为民主和包容的世界。时至今日,LGBT文学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文学一个主要而耀眼的门类。
LGBT文学可以追溯到古典时代。在二十世纪,E·M·福斯特、弗吉尼亚·伍尔夫、瑞克里芙·霍尔的作品中也都有同性内容,从那时起,同性就从文学的内部茁壮起来。伴随着LGBT运动崛起的LGBT文学诞生了一大批杰出的作品,有戈尔·维达尔的《城市与柱石》、詹姆斯·鲍德温的《乔万尼的房间》、珍妮特·温特森的《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》、安妮·普鲁的《断背山》、约翰·欧文的《一个人》等。
在今年年初,迪伦·托马斯奖得主布莱恩·华盛顿,其得奖作品《罗特》(Lot)中的很多短篇也是属于LGBT文学范畴里的。在最近几十年,LGBT元素已经成为主流文学的一部分,它再也不需要搭载在徒有通俗甚至烂俗的元素之上了。文学已经不需要恐同(homophobia),甚至恐同是文学要谴责的对象,前段时候布克奖基金会副主席艾玛·尼克尔森被作家们集体控诉就很能说明情况。
在6月“同志骄傲月”(Pride Month),美国两项重要的LGBT文学奖,即三角文学奖(Triangel Award)、拉姆达文学奖(Lambda Literary Award)揭晓。三角文学奖由美国同志出版协会The Publishing Triangle设立,奖项分为LGBT虚构文学、非虚构文学、女同/男同诗作、跨性别文学等。今年是它的第32届。拉姆达文学奖也有30余年的历史。
越南裔美籍诗人王奥深(Ocean Vuong)凭借处女小说作《我们毕竟绚烂而死寂》(On Earth We're Briefly Gorgeous)摘得三角文学奖虚构文学奖即Ferro-Grumley奖。本书由企鹅出版社出版,它在早先还摘得Goodreads的两项大奖。王奥深出生在越南,其祖父是赴越作战的美国兵,她的母亲出生后就被送进了孤儿院。“一个美国兵干了一个越南农姑。我妈就存在了。我就存在了。炸弹就没有了=无家=没有我。Yikes”,他在此前的诗歌中写道。《我们毕竟绚烂而死寂》丈量的是主人公小狗和记忆档案中的故乡、神经质且不会说英语的母亲、在烟草场的出柜的距离。在这部融报告文学、移民文学和书信体小说为一体的作品中,他对母亲说,我写作以走近你妈妈,而每一个字母都落到比你更远的位置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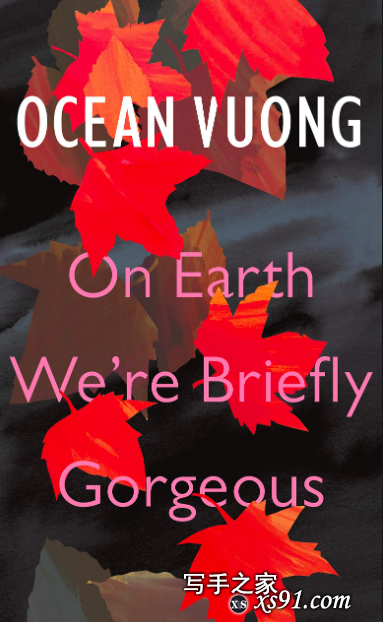
《我们毕竟绚烂而死寂》
王奥深毕业于纽约大学创意写作系,目前在马塞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负责一个MFA项目,他是2019年麦克阿瑟天才奖的授予人。他的处女诗集《有出口的夜空也有疤痕》(Night Sky With Exit Wounds)获得了T.S.艾略特奖,广受赞誉。其诗歌特色主要是减弱元音的存在、连缀词句。他的诗歌总是充满停顿的痕迹,从他的朗读中你很容易发现这一点。他的诗歌,或者说他的写作涉及的是成长中的自我经验,性、政治、写作,有自白派特色,但更简洁、更立体,不愧是安妮·卡森的学生。在一个访谈中,王奥深说自己最近在阅读李立扬的诗歌,其处女诗集《玫瑰》展现了在边缘中的瑰丽。
在骄傲游行(Pride Parade)的第50周年,《纽约时报》请几位LGBT作者讲述他们自己对于Pride Parade和LGBT的看法。刚刚获得普利策奖的杰里科·布朗告白了自己的同性恋史。他们在游行中认识,之后对方选择了成家生子,他记得他妻子得知此事后,两人大打出手的局面。老套的爱情破产后,他探索在性爱之外的种种,他不断回想起那些热烈的游行队伍。他认为抗议是行得通的。托马斯·佩奇·姆克贝(Thomas Page McBee),一位跨性别男性作家,认为骄傲是羞耻的反面。LGBT们在看不见的地方存在,但绝对不应被抹除。LGBT们也不需要用游行来证明自己。
华语世界的LGBT文学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其时,姜贵、白先勇、李昂等人都有重要的作品呈现。可是到了八九十年代,LGBT文学才成为一门显学,在中国台湾,酷儿文学也是在这个时期成为一个主流,这主要得益于其时的同志运动。在今日的台湾文学中,酷儿文学已是蔚为大观,邱妙津、郭强生、纪大伟、朱天文、洪凌、陈雪……2017年《联合文学》就曾推出《清热同志文学史》专号。
在《晚安巴比伦》中,纪大伟在语境上对酷儿和queer做出了区分,酷儿作为一个本土化的译词,它必须要镶嵌于本土故事之中。在他看来,酷儿也不同于同志,同志追求身份认同,酷儿则怀疑身份认同,“所欲所为是四处乱窜的,很难以单种认同加以统一”。酷儿文学寻求的是身份的异变与表演,欲望的流动与多样,因此酷儿文学和科幻、恐怖、性爱等元素都有交好。郭强生分享了类似的想法,他说:”同志二字对我来说,更像是一种迂回的美学,它不断向我揭露,身份是怎么被建构出来的。同时,我认为同志是一个提供人喘息的空间……就时空上,《断代》或许可以接上《孽子》……同志相爱的形式又是什么?我们对于爱的认识从何而来?我必须说,主流对爱的界定是删节版的,人们不会告诉你爱充满扭曲、变形、黑暗。”
已和恋人成婚11年的陈雪对爱情似乎更为达观。在答《联合文学》的访问中,她说:“我对着天地间所有的爪痕与豹尾复述,唯有跨越了人与物之间的惦念,才是语言所堪能触及又无法留住的所在……距离彼时的许久之后,我赫然领悟,原来自己被指派为守护使的角色。我将创造且滋养某个无与伦比的生命:祂/牠既是猫儿,亦是人儿;此外,祂更是某种尚未想像得出境的事物——历经许多百万年,罕有无伦的交合方可能所绽放的事物。”
反种族主义风波
随着Black Lives Matter抗议活动的进行,出版商不得不面对各种压力,同时族裔文学和反种族主义文学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。黑人作家和族裔作家们也纷纷在推特上的#publishing paid me#话题标签下面,吐露自己的艰难和苦楚,他们相信自己在改变着历史。诗歌基金会(Poetry Foundation)上周的遭遇似乎表明了某种转向。然而,沸腾在网络上的反而是千百种杂音。
为了抵抗这些杂音,J.K.罗琳、鲁西迪、乔姆斯基、阿特伍德等150多位作家在《哈泼斯》上发布一封公开信,向公众倡导公开辩论、言论自由和宽容。作家托马斯·查特顿·威廉姆斯(Thomas Chatterton Williams)说,特朗普是清销员们的头(Canceler in Chief),对他们的矫正不应丧失我们的规则。这些签名者们有的是左翼,有的右翼,有的是白人,有的是犹太人,他们相信人类社会分享着一些基本的价值。他们抵抗着如今兴盛而跋扈的“清销文化”(cancel culture)。
文学经纪人雪妮丝·费舍尔(Cherise Fisher)称上世纪九十年代是黑人文学的辉煌时期,但后来出版社就失去了愿意大批采购黑人文学的零售点。书籍的出版仍然是一个关乎市场的事情,投资、读者,这些都不是想象中的事情。作为一个黑人,或者一个现代的、进步的“超级黑人”,她仍然无法免于黑人读者群的想象和数据现实。
在风波中,2019年布克奖获奖小说《女孩、女人、他者》(Girl, Woman, Other)登上英国小说畅销榜榜首——随后它也被授予了英国图书奖。作者伯纳德·埃瓦里斯托(Bernardine Evaristo)是尼日利亚移民和英国白人女教师的第四个孩子。《女孩、女人、他者》充满政治意味,它探讨了英国黑人女性的状况。她希望可以拓展人们对英国黑人女性的想象。书中有些女性出身底层凭借自己的努力实现了阶层跃迁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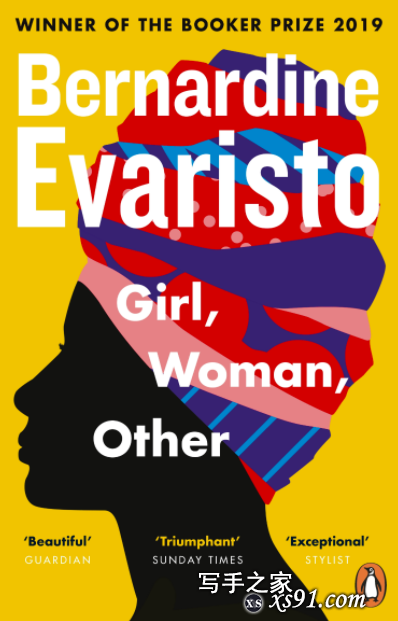
《女孩、女人、他者》
不得不说,桑戈尔们所定义的黑人性(blackness)在今日已经有了不同的意味了。
少数族裔作家们的出版困境和稿酬低下是一方面,他们所取得的成绩又是另一方面。在小说世界,杰斯明·沃德(Jesmyn Ward)的《拾骨》(Salvage the Bones)、《歌唱,不朽地歌唱》(Sing, Unburied, Sing)获得了2011、2017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;科尔森·怀特黑德的《地下铁道》获得2016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。基兰·德塞(Kiran Desai)的《继承失落的人》获得2006年的布克奖;马龙·詹姆斯的《七杀简史》获得2015年的布克奖。还有查迪·史密斯、奇玛曼达·恩戈兹·阿迪契……
在诗歌世界,自从罗杰·罗宾逊(Roger Robinson)的《移动天堂》(A Portable Paradise)获得了T.S.艾略特奖和英国皇家文学学会翁达杰奖之后,诗人们对黑人文学或少数族裔文学就开始有着更多的期待和憧憬。罗宾逊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的后裔,他的少年时代在故乡度过。如今他在伦敦做了很多诗歌工作坊和实验室。
诗人林顿·奎西·约翰逊(Linton Kwesi Johnson)和迪伦·托马斯奖获得者诗人凯尤·钦贡伊(Kayo Chingonyi)都是罗宾逊的拥趸。林顿提及杰恩·科特斯(Jayne Cortez)的政治诗歌《就在这里》,它是这样的结尾的,“如果我们不斗争/如果我们不坚持/如果我们不组织和联合/找到权力来主宰我们的生命/那么我们就会带上/受囚的狰狞表情/卑下的风格化表情/自杀者的古怪表情/恐惧的非人性表情/压抑的腐败的表情/永远永远永远/就在这里”。凯尤认为诗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神秘的能力,没有它社会就会僵死一团。
他们的诗歌有点类似于“表演诗歌”(Performance Poetry),它是即兴的、批判性的、观念分享的、社群共治的,总之是很符合现时代的诗之正义的。在最近几年,专门为黑人或少数族裔设立的诗歌奖也多了起来,伯纳德·埃瓦里斯托就设立了布鲁内尔国际非洲诗歌奖(Brunel International African Poetry Prize)。
新作几种
苏珊·豪(Susan Howe)的新作《和谐》(Concordance)仍然是鲜活的“语言派诗歌”(Language Poetry)著作。苏珊·豪的母亲是都柏林人、叶芝的学生、阿贝剧院的演员。苏珊出生于1937年,一个打字机时代,如今看来已是古老而笨重的打字机伴随她的一生,也渗透到她的诗歌写作中。她在青年时期没有进入学院和研究所里的打算,但后来她还是被学校邀请去授课。她曾经去纽约学画,这使得她的拼贴术相比于文字更接近绘画。在理论上,她将自己归属为90年代的客观主义者那一波,而非法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。在系谱学上,她继承的是庞德、威廉斯和克兰的诗学,她将其碎片化和新媒介化,属于安妮·卡森一代——尽管安妮·卡森要谨慎周全得多。她的诗歌在最低限度上没有语法,文体优雅精巧,在最高限度上则逼近了艺术。目前,她所取得的最高荣誉是2017年的古根海姆奖学金和2018年的格里芬诗歌奖。
《伊万和伊万娜奇幻而悲惨的生活》是瓜德罗普女作家玛丽斯·孔戴的作品,它刚刚被理查德·菲尔科克斯(Richard Philcox)译介到英语世界。在这部作品里,孔戴让两个双胞胎完成从瓜德罗普、巴黎、马里再到巴黎的几度迁徙,一股脑将当下社会面对的肤色问题、贫困问题、宗教问题、新旧殖民主义问题、种族主义问题、乱伦问题、恐怖主义问题、移民问题全都抛给了读者。孔戴出生在加勒比海的瓜德罗普岛,在父母的期望下,她去索邦大学就读,毕业后去几内亚等国做老师。她在1985年获得富布莱特奖学金赴美留学,并在1995年至200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法语。她在40岁才发表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,主要是因为她对自己的作品缺乏信心。她的作品的政治性极强。在访谈中,她对全球当下的问题持乐观态度,她希望变革会在不久的未来发生,“这需要时间”。
乔伊斯·卡罗尔·奥茨出版新作《夜晚。睡眠。死亡。星星。》(Night.Sleep.Death.The Stars.)。书的题目取自惠特曼的《一个晴朗的夜晚》,但它的内容却没有这么轻快和浪漫。这是一个反种族主义的政治故事,和正在发生的乔治·弗洛伊德之死及其后续正相协调。通过这部喜剧性的小说,奥茨的诉求是很明确的,麦克拉伦家族所代表的美国种族主义和精英主义正在危害这个社会。没有变革就不会有正义。“受害者几乎都是有色人种,白人很少成为被攻击的对象…… ”,奥茨写道。奥茨的著作多达100多部,这让她收获了美国国家图书奖、耶路撒冷奖等多种奖项,她在6月刚刚获得了德尔杜卡世界奖。奥茨很宠爱她的猫,莉莉丝。
布丽特·班尼德(Brit Bennett)的作品《消失的那一半》也是探讨种族主义的。它和《夜晚、睡眠、死亡和星星》的不同在于:它是从有色人种内部出发,它的背景往前置了一段时间,定在上世纪中叶。史黛拉和迪瑟蕾代表着非裔的两种选择,一种是混入白人社会,一种是在自己的社群内部。史黛拉将自己涂白的经历,也是牺牲另一半自己的经历,这也是书名的含义。布丽特在答《卫报》的采访时说,她喜欢历史和情感之间构成的张力。这部作品的改编权已被HBO购买,它的电视剧版本将在未来和观众见面。
马华文学
从金枝芒、萧遥天、姚拓,到黄崖、潘雨桐、张景云、温祥英、王润华、李永平,到温瑞安、张贵兴、方天,再到林幸谦、黄锦树、陈大为、钟怡雯、李天葆,再到欧阳文风、贺淑芳、林惠洲、胡金伦、黎紫书、方肯、梁靖芬、龚万辉、张柏榗……马来西亚华文文学构成了一个必要的文学共和国。
今年的联合报文学大奖便由马华作家张贵兴的《猴杯》摘得。今年的评审团由王德威、向阳、吕正惠、周芬伶、张瑞芬、杨泽、骆以军组成。张贵兴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不完全是马来西亚人。他说:“来台湾前,我是砂拉越的(第三代)华人……”,砂拉越是在1963年与诸国组成马来西亚,在此之前,它短暂地充当着英国殖民地。1976年,张贵兴赴台湾求学,并在1982年抛弃自己的马来西亚国籍。不过,他并不像李永平那样否认自己是马华作家。像婆罗洲的风候一样,张贵兴的写作也充满热带气质,语言精致、故事肥美,这在越来越大众化、文学奖化、杂志化的台湾文学现场显得很不合群。在一次采访中,张贵兴说自己要写最后一部长篇,背景设在台湾,以感念台湾收留他这个一无所有的流浪汉。
在今年3月接受《上海书评》采访时,黄锦树也承认“无国籍的马共成了无国籍的马华文学的一个隐喻或是容器”。自马来西亚建国后,马华文学作为单一民族国家之下的少数族裔文学就定调了,史氏的反离散论在此是不恰当的。“在地化的文化政治实践,在有国籍的马华文学出现之后,就已经不再可能。”对于马华文学来讲,“中国性”是一个“幽灵”的存在。而上述一切归根结底还是马华文学的自我认同问题。它的再述、它的失落、它的抵抗都是当下华语文学中一个并不前沿、但就绝不落后的文学现场。
在大陆更为知名的黎紫书于5月出版了自己的新作《流俗地》,被王德威评价为“柳暗花明的寓言”,自是不错。她在答《联合文学》时说:“《流俗地》以西马中部一个城市为背景,再以一幢位处闹市的组屋为根基,写一众寻常百姓再普通不过的生活和他们的人生。……小说里的人们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参与政治,他们只是活在了时间和历史里。”盲女阿霞在混乱和肮脏中保持着谨慎的洞察,兀自发着不凡的光。她说:“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写小说的人,对故事都失去一种该有的敬意,甚至多少表现得有点蔑视故事。”王德威在序言中写道:“《流俗地》就是匹夫匹妇、似水流年的故事,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,国族大义那类问题早就在穿衣吃饭、七情六欲间消磨殆尽,或者成为晦涩怪异的执念。……华人社会以内的世道人情再千回百转,其实是内耗的困局,华人社会以外的国家仿佛不在,却又无所不在。”和他人不同,黎紫书在追求和解,她还抱着更大的希望。
跨性别作家简·莫里斯出版了自己的日记
《哈利波特》的作者J.K.罗琳在网站(www.theickabog.com)免费连载她封存多年的作品《伊卡狛格》(Ickabog),中文版也同步发布。罗琳的新闻可不是这部新作,而是作者在推特上的言论,她素来以直言著称。
上月,罗琳在推特转载devex文章,说“‘会来月经的人’,我明明记得曾经有个词是形容这些人的。谁来帮我想想。Wumben?Wimpund?还是Woomud?”该言论被认为有对跨性别者恶意歧视的嫌疑。和罗琳同属一家文学经纪公司的四位作家,因该公司拒绝发表支持跨性别者权利的声明,与之解约,作家们表示,“只有阻碍着弱代表(underrepresented)群体享有平等机会的结构性不平等被挑战和改变时,言论自由才能存续。”这次的风波在早先时候已经有所展露。作为女权主义者的罗琳被视为是变排激女权分子(TERF)。
面对公开指责,罗琳在推特上发布一篇长文,痛陈自己早年的性侵丑闻和婚姻创伤往事。的确,从政治意义上讲,罗琳是一个反平等主义者,或许还是一位反民主者。不过,罗琳强调的不是社会性别(gender),而是生理性别(sex),且她认为sex是优先于gender的。她说:“如果生理性别不存在,也就没有什么同性相吸。……我理解并尊重跨性别者,但是抹杀生理性别的概念会让很多人不能有意义地讨论他们的生活。”她设想跨性别男性是生活在一个充满偏见和暴力的“单性空间”(single-sex space)而不得不选择了跨性别。
中国读者最熟悉的跨性别者或许是简·莫里斯,她以旅行文学著称。1972年,有了四个儿女的她将自己的“James”改成了“Jan”。在她晚年的作品《她他》(Conundrum)中,她说自己是在母亲的西贝柳斯的氛围中,明白了自己长错了身子。她写道,“我相信错生性别的冲动……远不止是一种社会性冲动,还是生物性的、想象性的,尤其在本质上是精神性的。……从童年的宗教性幻想中汲取了一种信念,即达到完美境界的最合乎人情的捷径是在妇女中的佼佼者身上——尤其在刚过绝经期的善良、聪明、健康的妇女身上。她们已摆脱了性机能的束缚,其他方面依然富于创造力,对于爱和情欲仍非木石,经验适度,全无野心而不失抱负。无论哪国,无论哪个人种,整个而言这个范围内的人是我最仰慕的:我得意的是,哪怕只是在后列,哪怕只在侧翼,我现在总算跨进了她们的行列。”在今年早些时候,简·莫里斯出版了自己最近几年的日记,《再思再想》(Think Again)。来源:澎湃新闻,作者:宰信 木荒经
|
|